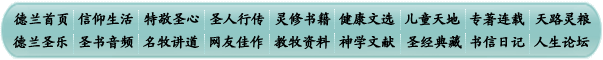|
我的朋友卡罗·加勒度请我把他这些本来是写给欧洲朋友的书信,介绍给英美读者。我觉得对于私人性质的默想加以批评是狂妄,这和我要公开讲述我们这份在沙漠中发展而臻于成熟的友谊是很尴尬的事一样。因此,请准许我推卸这项任务。不如就告诉你我认识卡罗的经过吧。 那是一九五九年十月,在马苏将军接管阿尔及利亚后不久。近中午时分,我终于来到达曼拉瑟的菜市场——深入沙哈拉沙漠。我在找寻五十年前富高建立的小兄弟会所。我一句阿拉伯话也不能说,而我说的几个法文单字:“兄弟”,“富高神父”、“教堂”等等,都完全得不到反应。于是我再试:“嘉禄富高神父?”马上有一群少年叫喊着“卡罗兄弟,卡罗兄弟”。他们一把抓住我的旅行袋,带我穿过马路,来到一个鞋匠的小店面前。 我要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间,才能完全意识到这个靠割旧轮胎编制耐用凉鞋为生的人,他的真正身份就是卡罗·加勒度,和我以前认识那位意大利“公教进行会”组织主要负责人加勒度,同是一个人。那时,这个组织,在教宗庇护十二领导之下,扮演着一个反共的政治角色。 好几年来,我强迫自己不要去想有关加勒度的事,因为我怕他的权利越来越大,更怕他现在以教友或神职人员的身份,成为支配意大利基督徒的、意大利民主党党员。 不错,这就是加勒度、我认识的加勒度。他现在已成为这些孩子,这些跛子和到富高坟地来的朝圣者的嘉禄兄弟了。 卡罗从他的小店钻出来,带我去看建在富高被谋杀地点的小教堂。富高由一个锦衣玉食的人一变而为一个苦行者;由一个军官变为一个修道士;由修道士变为一个神父、隐修士。一个法国贵族,要在这里,过着最穷苦、最卑贱的生活。他死在此地,因为他替法军守护十六根来福枪。在到小堂的路上,卡罗在一座墓碑前停下来。碑是由法军立的,上面写着: 富高子爵 耶稣小兄弟嘉禄 为法国效死 当我跪在卡罗身边,深陷在沙里和置身于平安的教堂内,碑上的字还阴魂不散地缠着我。在阿尔及利亚,法国就是帝国、最高权威,甚至是以极刑的代价才能换取的帝国。在阿尔及利亚,神父{极少数例外}等于法国殖民官和军队的随军司铎、在阿尔及利亚,做一个基督徒,不是等于使“和平”的意识型态成为消极隐退的理由就是——极少数——参加地下组织的理由。而在这里,在阿尔及利亚,我竟然还看到:“为法国效死”的字样。卡罗大概知道我在想什么,当我们离开小教堂时,他指着墓碑,简单地说:“如果你要像耶稣一样的生活,你就得准备像他一样被人误解。耶稣也是为一个民族而效死——照犹太大司祭的说法。” 我开始慢慢了解卡罗;这个死于权力的世界、为众人谋福的世界、唱高调的世界和政党的世界的人。我开始经验到他说他热爱主耶稣的话的真实性。我也深深佩服他直说真心话时的坦率,他一点不受外人批评的困扰以及他不怕被讥讽为幼稚的坦荡。他也不在乎别人因为他拒绝接受军务而批评他是个逃避主义者。 最初,他款待我,住在达曼拉瑟他的小店里。不久,他为我安排住在阿瑟蓝峰下一个山洞里,离他的小店约有两天的骆驼路程。他在洞里为我安置了一张床和用石头把风口挡住,以免我日夜被从几千尺高山上吹下来的冷风吹袭。 我们成为很投契的朋友。每次他来看我时,就给我说故事,每次想起这些故事,我就不禁要担心一日离开沙漠,这些故事就会显得格格不入。沙漠的无边无际,无论对强人或弱者,都是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压迫,回教牧童的歌声,唤醒了这位生活于严峻而清明的信仰之中的意大利人,他内心那种方济各式的温柔。沙漠的空无,使人学到几乎不可能的东西:欢怡地接受自己的无能。我怕脱离这样的背景,以及不认识卡罗本人,很多读者要尽很大的努力,才能了解卡罗亲口教我的这一切。 不过,我还是希望,至少有些读者读到这些文字的英文译本时(也在读完中译本后?)能找一天在完全静默中去体悟卡罗的话。他们可能根本不屑这样做。我希望他们会在一个英、美式的沙漠——在华斯大街或甘辛顿道上的一间孤寂的寓所、在医院、在病房,或在监狱里的一角、在火车的一角,打开这本书。 伊凡,伊力·墨西哥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