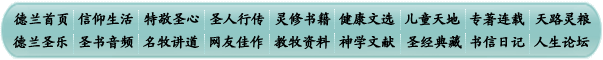|
一八 “我最亲爱的诸弟如晤:这是我在东京给你们所写的第一封信,我给你们报告,我们已平安地到达了东京,本教区属于道明会士管理。现在将我们旅途中所经过的一切,简略地给你们报告一下: “亲爱的姐姐:我毫不怀疑,我写给亨利和欧色柏的信,你一定也阅读了,这是一封报道的信,叙述我们由澳门到东京,旅途上所遭遇的一切。当我们到达东京以后,据人们的传说,如果我们迟走几小时的话,人们便要给你们报告我们死亡的消息。因为三只越南王室的船只,听说我们来了,将一只中国帆船团团包围住了,这只船曾经装载过我们的行李,他们在任何船的角落里仔细检查了一番,如同其他别的船一样,毫不放松,那么想逃脱他的手是不可能的。但是天主保护了我们,没有将我们交付给他们的手里,在这紧要关头,我们都正享受着阿加萨主教的优待。在这里我们住了八天,可是我完全在病苦中度过了。一位安南医师给了我几样补药,毕竟还能使我继续我的行程。 “当我谈及这里的医师和医药,你一定会感到奇怪,或许你想我是处在一个野蛮人的地方。但是,你当明了越南人的文化程度,在一些事上虽不能说胜过欧洲人,但是绝对可以和欧洲人并驾齐驱。技术方面,令人钦佩的实在不少,他们有许多高明的医师,在本国都是鼎鼎大名的。一位给我诊病的医师,当他摸了我的脉搏以后,立即肯定地说出了我的病源,是由肝脏错乱而引起的。我们拜辞阿加萨主教,去到赫茂瑞纳主教那里,他是一位极有圣德的高龄主教,和霭可亲,如同一根古老的圆柱,屹然立于崩圯的建筑之中。关于朴素美丽和热心,没有人可以和这位年近古稀的主教相比。当我们还在那里的时候,有一天,教区的首脑们,到他跟前抱怨着说,农人们都不愿缴纳什一税(他们称为童贞圣母税),用来维持一切堂口的开支,于是主教召集会议,将这件事托于圣母玛利亚的保护之下,俾能获得解决。农人们以今年歉收为辩护,就为了这个理由,主教一心袒护穷人们,穷人们终于获得胜利了。我们在主教公署,只住了两天,这里不过如同一间穷人的茅屋而已,用木材和泥土作成的,屋顶上面盖着茅草。一切的房屋都有同一的式样,因为这里的气候非常炎热,是以也习惯成自然,不以为意了。只要能阻止烈阳的薰蒸和风雨的侵袭,便没有其他的需要了。 “这里所建造的圣堂,根本谈不上华丽,不过是一间茅草屋而已,几根木材当作柱子,将它支撑着,只要房屋不至于倒塌,已经满足了。到了瞻礼庆辰,悬挂一些丝织品,算是圣堂里的装饰,算是我们的结彩,用几块木板搭成了一座祭坛,如是而已矣。如果我们的圣教会,在越南能享受一时的平安,无论如何,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建筑一些比较华丽的圣堂,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没有到建筑的时候,暂时将茅舍作为圣堂,也未尝不可以。不多几日以后,我们要起身往越南的中部,西班牙传教士主持的教区。我们由水路进发,可是风向不顺,狂风大浪无情地阻止着我们的前进。按照当地的习惯,我们便改乘轿子,我们经过许多教外人们的村落,有一次,我们经过一座大镇,当我们行到市区的中央,来到了一座官吏的住宅前面,他是本地的大老爷,照当地的风俗,所有的旅客,经过这里的时候,除了是他的长官以外,人人必须步行,以表示对他的敬意。我们不敢遵照这种习俗,怕使那在场群众认识我们,我们的轿夫立即加紧步伐,往前飞奔。突然间,在我们的后面,听见一阵呼唤声:‘你们是些什么人,路过这里,竟敢如此无礼?’一位传教员代替我们回答道:我们是他家里的病人。哨兵又道:‘至少要鞠躬致敬,’轿夫不得已,只得俯首从命。雷克南神父,因为他懂得他们所说的话,已经吓得面色苍白了。反之,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所遭遇到的危险,以为要我们快走,于是我很高兴地拨开我的两腿,预备开步走了。侥幸得很,轿夫没有让我走,如果他们来检查我们的话,我们轿夫急忙抬起我们往前飞驰,那么我们的命运便不堪设想了!之后。我们来到一条小河边,在河里停泊着几只教友的帆船,我们很愉快地跳上了船头。船夫将我们安然送到狄阿斯主教的公署那里,他是宗座驻东京的代表。两个力夫,早已在那里等候着我。雷度德主教特别派遣他二人,为护送我们到达目的地。在这里我们受了西班牙人优渥的款待,休息了几天后,不能不向他们珍重告别,而踏上了我们旅程最后的一段。这段路程上的危险,丝毫也没有减少。在朦胧的夜间,我们踏上了一只帆船,这只帆船必须经过一个城堡,在那里,常有四五百兵士防守着,负责保卫国王的粮仓。凡过往的船只都逃不过他们的监视。当我们的小船,来到城堡对面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吆喝的声音,问我们是什么人,船老板即回答道:‘我们都是政府的官员。’兵士们不信,呼声立即传到我们的耳鼓里了,一刹那间,发现一只小船,在我们的船背后追来。侥幸得很,风势很顺,我们总是隔着相当远的距离,他们的船终于不能追上。在我们的后面,却来了别的一只船,载着我们的行李与仆从。为此他们和追赶我们的敌人双方在船头上酣战起来了。不过我们的仆从,极奋勇地保卫自己,敌船不能招架,终于逃遁了。亲爱的姐姐,这便是我写给你的报道,我们去东京的沿途情形。在这里,一般说来,乘夜行路,大抵比白昼安全一点,如果由水路的话,无论是小河或运河,只要时常更换船只,也未尝不安全。如果走陆路的话,乘着舆轿,如同有权有势的贵族一般,旁边以草席遮盖着,行人也不至于瞧见的。有时非赤足步行不可,因为,禾田里,仅仅有一条窄狭的人行道。如果白昼行路的话,倒有很好的机会逃避路途上的困难:可是,夜间经过丛林的时候,却必须十分留意,否则不知不觉便将陷身‘窟窿’内,或是踏入禾田里去,欲找立足的地方,那是不可能的。当你正在滑冰的时候,你的脚常在光滑而富有湿气的地上,如果不谨慎,或许也要使你跌倒吧!你想,这为徒步旅行的人们,是一条非常写意的路吗?那么,这样的路,若说是毫无疲劳,我深信你必定大笑,因为我作了滑天下之大稽的主角。 “本月十三日,我们抵达了自己工作的新园地。我首次拜见了宗座代牧雷度德主教,他的大名在传教集志内,你一定时常见到的,现在他非常忙碌,正在给一位将晋铎的修士,举行退省神工。他的助理杨特蒙席,又是东京教区的副主教,正在这里辅助他。别的两位传教士,已经起程履新了。在东京有四位司铎已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了……我既是其中之一员,我感到如何的快乐,你是万万设想不到的。我们这里是多么的简单朴素,诚实坦白——我们的上司,对我们是多么的谦虚和善,这使我们立即感觉到,我们好似早已相识的一般,凡是我们想象得到的问题,无不谈论——法国、罗马、俄国的内战等等,都是我们谈话的资料。当我们离别以前,我们都团聚在一起,唱一些我们娴熟的歌曲和法国的国歌。’ 过了不多时以后,我们的这位传教土,给泰勒神父写道: ‘在雷度德主教这里,你想我遇见了谁呢?原来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翟烈神父,在一年前,从我的眼眶里,不知流出了多少离别泪,唉,泰勒神父啊!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在赏心悦目的东京,已经一月了,老实告诉你,我住在这里非常愉快。翟烈神父讲道理听告解,在他的心灵内,工作的爱火,熊熊地燃烧着,他的身体仍然健康如常。我身体的健康,固然不是上等的,可是,患病与否又有何关系?俗话说:‘身体瘦弱者,得享长寿。’料想你也知道吧!这样,我也可以自慰了。奋勉吧!下面是圣女大德兰的箴言,是我时时诵念的:勿让世物扰,勿容俗务缠,万事如流水,唯主永不变,忍耐胜一切,有恒意志坚,倘尔怀吾主,可如磐石安!’ “现在,我们所有的财物,都被外教人掠夺去了,是以,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有了天主,便有了万有,什么也不缺乏了。我一到东京,便去拜谒潘纳德神父的坟墓,他的遗骸埋在本校的圣堂里,靠近祭坛的旁边。” 如果卫纳尔神父在东京的时候,能遇见他的老朋友泰勒神父的话,则其愉快,也必和遇见翟烈神父时一样。 翟烈神父给泰勒神父写道:“谁曾说过或想念过如此的幸福呢?虽然似乎不可能,可是已成为显明的事实了。在东京教区的西部,我和卫纳尔神父竟能邂逅相遇,住在同一个的村里,同一个的住宅里,同一个的房间里!呀,真难描写这次重逢给予我们的喜乐和愉快!不过,你既不能与我们同乐,恐怕你的心要破裂了吧!但是,你应善自排解,不要自寻苦恼,你信任我的话吧!卫纳尔住在这里,只有一月的功夫,他已开始学习越南语,并且成绩相当可观,发音方面,也相当准确。他说话时,态度温文尔雅,真可谓天生的语言学家。此地一切如常,可以释念;我以一颗至诚的心,恭祝你们和我们东京教区的传教士,一样快乐,一样平安!” 卫纳尔神父开始工作了,这便是他无上的愉快。他最爱他的本堂区,在他的一首热情奔放的诗里,可以看出来。这是一首从他心灵的深处,流露出来的诗,充分地流露出他整个生命的期望,那便是:工作,救人,死亡。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