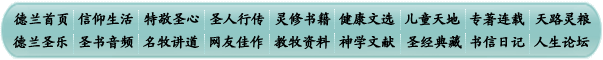|
到目前为止,关于对动物造成痛苦我说了许多,可是还没有提到杀死动物的问题。这个做法是有意的。用平等原则来处理制造痛苦的问题,至少在理论上相当单纯。疼痛与痛苦本身便是坏事,应该防止或者减少,无论感受痛苦的对象属于什么种族、什么性别、什么物种。一次疼痛有多严重,要看它有多强烈、持续多久,强度与长度一样的疼痛便是一样坏的事,不管感受者是人还是动物。 但是杀害一条生命的错误,要来得更为复杂。在本书里,我将不直接探讨杀生问题,因为就 当前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残虐暴政状态而论,对于疼痛与快乐做平等考虑的单纯原则,已经足以让我们指出并且抗议人类对动物的一切主要虐待行为。不过,关于杀害仍有必要略做交代 。 大多数人都是物种歧视者,不忌对动物造成痛苦,却不会愿意因同样的理由对人类造成同 样的痛苦;与此类似,大多数人都是物种歧视者,不忌杀害其他动物,却不会愿意杀害人类。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讨论须要更为谨慎,因为正如关于堕胎以及安乐死的持续不 断争议所显示的,人们对于何种情况下杀人是正当的,持有极为不同的看法。而对于杀人为何是错的、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有理由杀死一个人,道德哲学家也没有一致的想法。 有一种看法,认为杀害无辜之人类生命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错的,我们先来检讨这种看法。 这种看法,可以名之为“生命神圣观”。采取这种看法的人,反对堕胎及安乐死。不过他们一般不会反对杀害非人类的动物——因此也许较准确的称呼应该是“人类生命神圣观”。认 为人类生命——并且惟有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乃是一种动物歧视。何以如此,从下面的例子可以见出。 假定一个有时的确会发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婴儿生下来脑部就遭受大幅度而无法治疗的伤 害。伤害极为严重,这个婴儿注定永远是个“植物人”,不可能说话、认人、独立活动、或者发展出自我意识。双亲了解不能指望这孩子的情况有任何改善、同时根本上也不愿意自行 负担或要求国家负担每年多少万元的照顾费用,遂请求医生以无痛苦的方式将这个婴儿杀死。 医生应该照这对父母的请求做吗?在法律上,医生不可以做这种事;在这方面,法律反映了生命神圣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可是针对上例中的婴儿有这种观点的人,却并不 反对杀害人类以外的动物。他们能证明这种差异的判断是合理的吗?成年的黑猩猩、狗、猪 、 以及其他许多物种的成员,无论就与别人沟通、独立活动、自觉等能力而言、或任何其他可 以合理称为给生命赋予价值的能力来说,都要远远超过上例中脑部受了严重伤害的婴儿。即使受到最仔细的照料,一些严重智障的婴儿也永远不会达到狗的智力水准。我们也无法借用 上例中婴儿父母的关怀来立论,因为在这个假想的例子中(以及在一些实际的例子里),他们 自己也不想让这个婴儿活下来。在主张这个婴儿拥有“生命的权利”的人眼里,这个婴儿与动物不同之处,仅在于它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属于智人这个物种,而黑猩猩、 狗、猪则不然。但仅以这一项差异为据,赋予婴儿生命的权利,却不给其他动物同样的权利 ,当然是赤裸裸的物种歧视。它和最原始、最露骨的种族主义者恣意设定用来支持种族歧视的差异,其实并无二致。 以上的说法,并不表示我们一定要主张杀死一只狗和杀死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一样错误,才不 算物种歧视。要知道,只有当我们完全按照人类物种的界线划出生命权利的界线,才算是无可救药的物种主义。主张生命神圣观的人正是如此,因为他们在严格区分人类与动物之余, 并不承认在人类物种之内也可以做区分,从而他们强烈地反对杀死严重智障者以及衰老痴呆无救者,一如反对杀死正常成年人。 要避免物种歧视,我们必须承认,在一切相关方面均相似的生物,便有相似的生命权利—— 仅仅在生物学意义上身为人类这个物种之成员的身份,在道德上并不是这项权利的一个相关标准。在这项限制之内,我们仍然可以主张(例如)杀死一个正常成年人,要比杀死一只老鼠来得更严重;我们的理由可以是因为前者具有自觉能力、能够计划未来、与他人发展有意义 的关系,而后者咸信并不完全具备这些特色;可以是因为人类拥有紧密的家族以及其他私人关系,而老鼠的家族关系等并没有高到同样程度;也可以是由于其他人会受到的影响构成了 关键性的差异,因为杀死正常成年人会令其他人担忧自己的生命;更可以是根据这些理由的某种混合、或者与其他理由的混合。 不过,无论我们选择的标准为何,我们都必须肯定这个标准并不与人类物种的界线完全吻合 。我们可以正当地主张,某些生物所具有的一些特色,使它们的生命比其他生物更有价值;可是无论根据的标准是哪个,某些人类之外动物的生命,无疑会比某些人类的生命来得有价 值。举例来说,一只黑猩猩、狗、或者猪自觉的程度、或者与其他人建立有意义关系的能力,都要胜过一个严重智障的婴儿或者极度衰老痴呆的人。因此,如果我们认为生命权利的基 础在于这些特色,我们就必须赋予这些动物与这些智障人或衰老痴呆人同样甚至更多的生命权利。 这个论证的结论有利有弊。你可以说它证明了黑猩猩、狗、猪、以及其他一些物种拥有生命 的权利,任何情况下杀死它们都是严重的道德过失,即使它们年老病痛、并且我们的用意只是要使它们解脱痛苦。但是你也可以认为这个论证证明了严重智障者与衰老痴呆者没有生命 的权利,可以因十分普通的理由加以杀害,一如我们目前杀害动物一样。 因为本书的主要关切在于与动物有关的伦理问题,而不是安乐死的道德与否,我不拟对这个 问题做定论。不过我相信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立场虽然都避免了物种歧视,两个立场却都有 失妥当。我们需要的是某种中间立场,不堕入物种歧视,但既不把智障者与衰老痴呆者的生 命贬抑到像目前狗与猪的生命一般低廉,也不把猪与狗的生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连用安乐死让它们解脱痛苦都不可以。我们必须把人以外的动物列入道德关怀的范围之内,不再认为 为了人类不管多么无聊的目的,都可以把它们的生命牺牲掉。但同时,一旦我们了解到,单凭某个生物是我们自己物种的成员这个事实,无足以证明杀死该生物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错 的,我们或许可以对于不计一切代价维持人生命的方针——即使这个人的生命不可能再有意义、他的生存已不可能避免严重的痛苦——开始重新考虑。 据此,我的结论是,拒绝物种歧视,并不涵蕴一切生命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不错,自我意识 ,对未来有所规划、期望、向往的能力,与他人发展有意义的关系之能力等等,对于造成痛苦这个问题毫不相干,因为疼痛就是疼痛,无论当事的生物——在感受疼痛的能力之 外 ——具有什么能力。可是对于杀死生命这个问题来说,这些能力是相关的。一个生物如果具有自觉、有能力从事抽象思考、规划未来、进行复杂的沟通活动等等,那么说他的生命比一 个不具有这些能力的生物来得有价值,并不算是恣意专断。造成痛苦与杀死生命这两个问题有别,其间差异可以从我们在人类内部做选择的方式看出来。假如必须在拯救一个正常人和一个智障人的生命之间做抉择,我们大概多半会选择拯救正常人的生命;可是假如要在防止正常人的疼痛与防止智障人的疼痛之间做抉择——我们可以假想,这两个人都受到了某种虽 然痛苦但是不会造成大碍的伤害,但是我们所有的止痛剂只够一个人使用——该怎么抉择就没那么清楚了。当我们考虑其他物种的时候,情形也是如此。疼痛之为一件坏事,就其本身 而言,并不受到感受这种疼痛的生物所具有的特色的影响;可是生命的价值,却受到这些特色的影 响。这中间有差别的理由之一,就是杀死一个已经在展望、计划、追求某个未来目标的生物 ,不啻剥夺了他实现这一切努力的机会;可是一个生物如果没有能力了解他有未来可言—— 更说不上替未来做计划——那么将他杀死并不可能造成这种损失。 通常,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必须在一个人的生命与一个动物的生命之间做选择,我们应该选择 保留人的生命;可是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出现,相反的抉择才能成立,例如当事人并不具有正常人的能力。这个立场因此不能算是物种歧视,虽然乍看之下它有此嫌。在必须做选择 的时候,我们在通常情况里会选择保留人的生命而放弃动物的生命,乃是因为这种选择的根据在于正常人所拥有的一些性质,而不是在于他们属于人类物种这件事实本身。也就是因为 这个原因,当我们考虑的是人类物种之中缺乏正常人之特色的成员之时,我们无法说他们的生命在面临选择时一定得比其他动物的生命优先。这个问题,在下一章里会以非常实际的形式出现。不过,一般而言,对于在何种情况下(无痛苦地)杀死一个动物是错的这个问题,我 们无须提出一个精确的答案。只要我们记得,对于动物的生命,我们应该如同对于在心智能 力上居于同等层次的人的生命一样尊重,我们便不会太离谱了。 话说回来,本书所主张的结论,所根据的都仅仅是尽量降低痛苦这个原则。认为无痛杀死动 物也是错的想法,可以给这些结论额外的支持,不过严格言之并非必要。说来有趣,连我们应该改为素食这个结论也是如此,虽然在一般人心目中,此一结论的基础通常在于某种对于 杀生的绝对禁止。 我在本章里采取的立场,读者也许已经想到一些反驳。举例来说,对于可能伤害人类的动物 ,我准备建议什么对策?我们是否应该设法阻止动物相互杀害?我们怎么知道植物不会感到疼 痛?而假如植物会感到疼痛,我们岂不必须饿死?为了避免扰乱主要论证的发展,我打算特辟一章探讨这些反驳。急于知道如何回应这些反驳的读者,可以先读本书第六章。 以下两章,将探讨物种歧视的两种运作实例。我以这两种实例为限,因为如此才有足够的篇 幅做较为透彻的讨论。不过在这种限制之下,别的纯粹因为人类未能正视其他动物之利益才会存在的做法,本书将完全不可能处理到。这类做法包括了以娱乐或毛皮为目的的狩猎; 养殖貂、狐及其他动物以取其毛皮;擒捕野兽(往往要先射杀其母兽)关在狭窄的笼子里供人 类观看;折磨动物让它们学会马戏班的表演;折磨动物以供牛仔技能赛的观众取乐;假托科 学研究之名用“爆裂鱼叉”屠杀鲸鱼;用鲔鱼船撒的网每年溺死十万只以上的海豚;在澳洲内陆每年射杀三百万只袋鼠去生产皮料与宠物食物;以及随着人类在地球表面扩张我们的混凝土与污染帝国时,对于动物的利益的普遍忽视。 对于这些事,我将几乎不会触及,因为如我在本书新版序言里所言,这本书并不是一册资料 大全,收罗人类对动物所做的一切恶行。相反,我只选用物种歧视付诸实行的两种主要例子。这两种做法并不是孤立的虐待狂实例,而是制度化的运作,每年所加害的动物数目分 别要以千万计和以数十亿计。我们也无法声称自己与这些做法毫无牵扯。这两种制度之一— —动物实验——受到我们所选出来的政府的鼓励支持,其经费也多半来自我们所缴纳的税金 。 另外一种制度——养殖动物作为食物——之所以有可能,完全是因为大多数人购买、食用这套制度的产品。我特意挑选这两种形式的物种歧视来讨论,原因即在于我们无法卸责。这两种实例其实是物种歧视的核心。遭它们荼毒的动物数目、以及这些动物所受到的痛苦程度,超过了人类所做的其他任何事。要将这两种做法停止,我们必须改变政府的政策,也必须改 变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如果这两种由官方提倡、并且几近普世接受的物种歧视做法能够废除,其他的物种歧视做法的废除,也就不会太远了。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