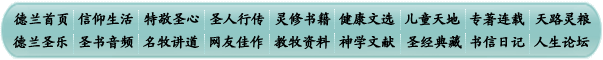|
《作弟子的艺术》:热罗尼莫神父由他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能够让我们在神修之路上安全地前进的诸多好建议。当然在我们把它们转化成为自己的个人化经验的同时,也希望我们在可能范围内,再把它们传给后人。 当热罗尼莫神父病逝的时候,我正怀着歉疚的心情在别处参加一次研讨会。会议期间,当然了,好些人带来了他们“善度隐修生活的见证”。就像应该是事实那样,只要有人谈及最喜爱和最亲密的事时,他们都作证说祈祷是他们的强项。为祈祷生活作见证。开始时,我分心走意的听着,左耳入,右耳出,但是慢慢地,我感兴趣的事又重新来了。我猜想那时热罗尼莫神父并不是他实际所是的那么疲惫,因此我给他写了一封短信,让戴奥法纳弟兄念给他听:“……实质上说,这位约五十岁的修女,这位好像对自己很肯定的修士,这些修女或这些修士,都是利用开研讨会的机会,躲避隐修院的严厉生活,或者说换换空气;当他们开始谈及对他们最宝贵的东西时,他们都说是祈祷,而且他们关于祈祷所说的,大致与我们的说法相同。不同点仅仅在于当这个修女还年轻的时候,长时间地跪在圣体台前祈祷时,却因不知道怎样做而心烦意乱,心急如焚,但是在她的前后左右没有任何前辈指给她应循的正路。这个当年二十岁时就进入修院的修士,在他的初学期间,也同样没有任何人为他指破迷津,因此为了能够自我培育,他不得不采用东拼西凑的方法,来拾取有关祈祷的信息。从这个人偶尔得到一些建议,从某人的讲座里听取了一些说法,从某本书中读到了一些关于祈祷的理论,他们只能跟在那些机会性的讲道者的屁股后面,像拾取被忘记在地里的麦穗一样,毫无系统地收集零碎,收集下脚料。随着人们在这方面的见证的增多,我突然醒悟过来,意识到他们和我唯一不同之处,来自我初学时便遇到了您这个特殊的事件……”读完了我的信以后,热罗尼莫神父对戴奥法纳弟兄说: “你们的神师对我很好。然而,为了能够有真正的老师,必须有一些愿意受教的心灵!” 我自己是否曾经是一个合格的弟子?这是另一码事!然而热罗尼莫神父的话里暗含着他自己曾经不断地重复给我们的,追随旷野之父们的芳踪的精髓: “当弟兄们不仅向长者请教,而且把他们的教训付诸实行时,天主自然会启示长者应该说什么。但是现在,既然人们只是来请教,而不再实践他们的教训,天主已经从长者身上收回了讲话的神恩。” 热罗尼莫神父很喜欢把圣热罗尼莫《厄则克尔先知书注释》中的一段给我们做写听: “一个神修指导者,如果由于害怕危险,或者对罪人的得救失望,而不愿意指导某人,教育某人,他就冒着丧失自己灵魂的极大危险:因为他如此做,使他自己成为某人丧亡的负责人…… 我们应该懂得,不论指导者或被指导者,二人都享有完整的自由。因为讲话或者不讲话完全取决于指导者的自由意志;而被指导者也可以自由地听取教训,实行教训,而因此他们的得救得到保障。或者相反的,他们也可以轻视、鄙视教训,因着他们的漫不经心,而导致他们的丧亡。但是,切记不要匆忙下结论:‘如果被指导者根本就不愿意实行他们听到的教训,那么我们教育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每人都要按照自己的基本抉择、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内心的准备、自己应该完成的义务而受审判。既然您已经领受了告诫、劝导人的使命,如果您应该发言而没有发言,您就应该负罪;至于对方,如果他拒绝听从您的告诫……” 直到他生命的末期,热罗尼莫神父一直把他这种聪明而且平静的隶属、依附态度视为神修生活的基础和不可或缺的条件,以至于为他而言,没有它,就没有神修生活。他去世前几天,还曾经对我们说: “我们神修人,必须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为了能够在我们身上完成这个艰巨的工作,应该让一些诚实而且能够胜任的神父——他们懂得神修生活的原则,也认识通往天主的道路——来帮助我们。很多的人白白的浪费掉了他们所付出的很罕见的心火、热情、慷慨的心胸,而一无所获。竭尽全力的推,而想让天国前进是不可能的,天国反而会越来越远离,因为他们并没有留在天主愿意他们在的位置。后者更坏的结果是,可能他们并未意识到,我却深信不疑,就是他们中的某些人打着耶稣的名号和旗帜,内心却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计划和野心。所以绝对不应该仅仅凭着您自己兴趣的判断,按照他们外在表现出来的才能,而把这些年轻人引向这两种错误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应该首先严格地分辨他们的圣召,分辨天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选择!” 热罗尼莫神父的神修谈话 1985,1,17 热罗尼莫神父引用良·伯乐的话指出我们生活的大原则说:“不论外在环境如何,首先应该把不可见的天主,不可见的事物放在可见的事物之前,把无限超越的天主,超性的事物放在本性的事物之前。如果把这个原则运用于我们所有的行为,我们知道您将会充盈着天主的力量,沐浴着深深的喜乐,沉浸于内心的欢乐之中。”或者他也简单地给我们如此重复: “永远要运用我们的理智,尽可能真诚地生活我们的每一天。” 人们关于热罗尼莫神父给我提的问题中,最让我动心的是一个很长时间以来就认识他的彩色玻璃窗画家的问题:“请告诉我,既然您与热罗尼莫神父的关系是那么得近,您知道是否他也如同我们一样遇到过怀疑信仰的时刻,他是否也遇到过关于天主存在的问题,生命的意义的问题,和他的圣召的问题……”现在,我没有能够立刻回忆起当时我怎样回答了他。经过思虑之后,我想我的回答应该是这样的:在他生命后期的十五年间,我经常和他在一起。当我初次认识他时,他已经六十二岁。至于他所经过的危机,在他已经写过的一些东西里,和他内心深处的表白中已经谈的足够多了。然而在我和他共同生活的那十五年内,尽管他仍然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和考验,但是我认为他从未怀疑过什么,因为在这些年中,我亲眼看见他与天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加强。 我现在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谈谈这个主题。在做初学神师以前,也就是说在没有负责接待和培训初学生以前,我经常自问为什么教会、教宗,神学家都很关心伦理生活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以一种我觉得不合适宜的、过度精确的方式,呼吁甚至命令人们遵守自然道德律和基督教道德律的重要原则。就在此时,我被任命为初学神师。在七年内,我接待过很多的年轻小伙子,其中有十二个人留了下来,愿意作隐修士。由于这个工作,我的观点完全改变了。慢慢地我发现那些内心最平衡的年轻小伙子(当然了,人性的平衡总是相对的,经常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牢靠的)都来自和睦的家庭,来自淳朴、简单的家庭,尤其是那些信仰很深的家庭,用‘淳朴、简单的家庭’,我并不想说一定是那些贫穷的、没有文化的家庭,而是那些不自视清高、不过分追求奢华的、诚实的家庭。我们的时代,转面不顾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竭尽全力,像逃跑一样的尽速远离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更可悲的是,与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的伦理态度却被推崇、被视为是正常的事,因为造成很重要的心理影响。因为为了生育,并不只是要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够了,而应该有一对夫妇,在他们之间还应该有彼此深沉的爱。他们也必须建立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中,也必须具备能够保护孩子,使孩子健康和谐的成长的气氛,因为我们是非常脆弱的。我们自私自利的欲望经常胜过我们慷慨大方的意愿,使我们抛弃基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经常想,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彼此分离时,他们或者瓜分,或者抛弃他们的孩子,那只是他们自己的私事。同样,一个女人愿意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孩子,而且愿意单独抚养他,那也仅仅是她个人的事,她有那项权利。而且如果一个女人不能够怀孕,而让另一个女人来代替,为了那些不如此就不能生育的夫妇是多么幸运!还有同样的很多问题,我们都是照样认为的。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孩子不仅仅是由血和肉而诞生、而形成的,即使在某些情况中,他也不是医学的伟大成就和科学研究成果的杰作。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在自己的身体内拥有尚未成孕的孩子,而我们的孩子很可能在心理上比在身体上更与我们相似。为了明了所有的这一切,应该有信仰,或者有非常非常深的伦理意识。为了能够看清事实的真相,应该让信德来光照我们。我的同代人,当然了,更不必说上一代人,他们都把基督徒信仰比较严格的要求视为压抑他们的人格,视为非常压抑人性的东西,视为没有基础的伦理规则的连篇废话。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这样! “今天的人,真正独立自主的人,总想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中的一切事。他所出的境遇总是不合他的心。他总是想改变什么。同样他也把一切已经肯定的事认为是有问题的,他甚至声称对他自己的存在,自己的位置都有疑问。为什么?因为他不再信仰一个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爱他的神。他不再愿意相信全能的天主时时刻刻在看护着他,天主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上,完全如同祂在地上所要经过的所有的事上一样精心地看护着他。时髦的成年人几乎不再相信: ‘天主,在茫茫的黑夜里, 注视着一只黑色的小蚂蚁, 慢慢地在一块黑色的石头上爬行、寻觅。’ 因为今天的人总想改变他的位置,改变他的命运,改变他的崇拜对象或者说偶像,改变他所宠爱的东西,而且愿意永远变换个不停。然而天主的朋友却应该保留并且保持、珍惜天主所给予他的位置,安放他的位置。事实上,在天主的朋友和世界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决裂的关系。一方选择的事物,另一方则要拒绝。否则,就不会有两个阵营的存在,而只是一个阵营:世界。” 摘自热罗尼莫神父未出版过的文章《我对于现时代的政治观点和策略》
|
|
||||||
    |
||||||